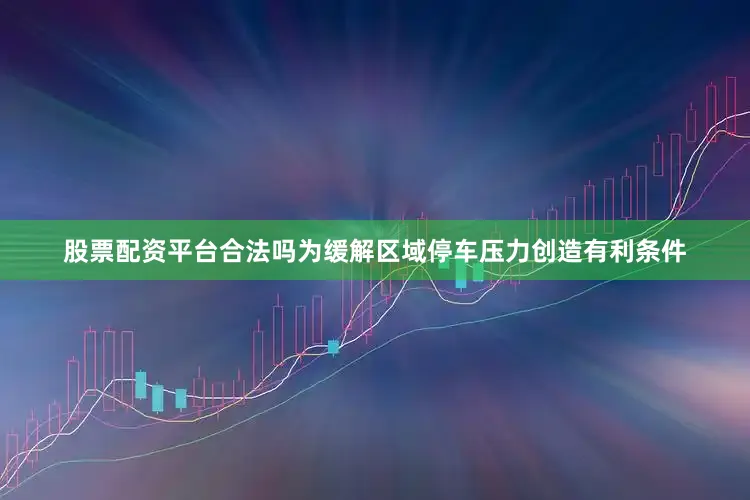北方高原部分大型遗址分布示意图:1.石峁 2.芦山峁 3.后城咀 4.白崖沟 5.碧村 6.府谷寨山 7.陶寺
仰韶文化首先兴起于黄土地区南部的河谷盆地,然后不断地向北面和西北面的高原山地传播扩散,整个黄河流域主要就是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下游平原丘陵地带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并存的格局。随着逐渐发达起来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向中原的持续扩张和冲击,加上自身的发展变化,陕晋豫邻境地区兴起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结束了仰韶时代,以陶鼎、斝、釜灶等炊器的流行为标志,开启了大中原区的龙山时代。
黄土高原地带的“大仰韶文化”,在漫长的存续时间里,始终以尖底瓶和各种盆、钵、罐为基本陶器组合。在不断西进的大汶口文化的冲击下,后续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仰韶文化传统,新出现斝这种空三足器,流行鼎、斝、釜灶为组合的炊器,且尖底瓶演变为平底瓶(也称喇叭口折肩罐),其他盆、钵、罐类陶器也有相应的变化,种类增多。该文化兴起于陕晋豫邻境地区(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等相邻地区),然后很快向周边传播扩散,其中往西沿渭河流域(包括支流)、往北沿汾河流域传播最远,影响最大。以斝的出现为标志,加上相应的变化,北方高原开启了龙山时代。(《 从芦山峁到石峁——北方高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 》作者: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
展开剩余93%至今为止,那些研究机构已经检测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古DNA,标本量特别大,如上图所示
至今为止,那些研究机构已经检测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古DNA,标本量特别大。理论上,测量次数越多,平均值越接近真值。根据考古DNA,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华北地区及其山东一带发现了很多N-M231,中晚期开始出现了O-M175,南方新石器中期至末期出现了很多O-M175、但N-M231极为稀缺。已知K2a2b(NO)-M214有两大分支:N-M231与O-M175。黄淮海平原N-M231与O-M175共生共存,下游分支多样齐全,多样性极高,暗示NO-M214早期分化地点可能是中国东部,向周边地区扩张。
不难看出,中原仰韶晚期古DNA基本上是O2a2b1-M134的下游分支,多样性低,比较单一,而大汶口古DNA有O2-M122的不同分支,包括O2a2b1-M134(M117、F114)、O2a2b2-N6(旧称AM01822)、O2a1a-F1876、O2a1b-IMS-JST002611,多样性非常高,暗示着:两万年前O2-M122最可能是起源于中国东部及其泰沂山脉南侧与淮河之间的一带,从东至西迁徙分化,然后向北方、南方逐渐扩散,比如齐家文化O2a2b1-M134、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墓主O2a2b1a1-M117、广西独山人O2a2a1a2a-M7支系F1275、福建溪头村遗址O2a1-L127.1,他们各自的单一支系多样性很低,由于远古人骨DNA片段不全,无法细分具体下游,故不能看作原始祖型。
O2-M122在黄淮大平原上进行农业技术革命,诞生出很多不同的下游分支,实现农业人口大爆发,形成了城邦工业人口,但由于土地占有权、资源有限性和人口过剩问题,导致O2-M122内部竞争,下游分支远迁谋生,不停繁衍,最终覆盖了亚洲大部。简单地说:O2-M122祖地多样性高,下游分支远迁之处多样性低。
在全国除山东地区以外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与龙山文化时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或有联系的文化遗存,并大多都曾经被命名为以省称开头的“某省龙山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良渚遗址曾经被命名为“山东龙山文化杭州湾类型”、“浙江龙山文化”。
1981年,严文明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即《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章指出:“现在人们所说的龙山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合体,其中包含着许多具有自己的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领域的考古学文化……但绝不能因此而对它们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有任何的忽视。因此我还是主张应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并且建议称之为龙山时代。”严文明先生的这一主张很快被学术界接受。
可见,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的影响具有革命性,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研究者通过大范围的比对研究指出,大汶口晚期的扩张影响的范围涉及到中原地区、北方地区、良渚、石家河。自此启动的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张海、赵晓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大汶口文化因素在中原及其南北地区的广泛传播,开启了龙山时代,其最初由多个区域文明融合组成,海岱文明、中原河洛文明、江汉文明以及东北的燕辽文明。“多元”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一体化”的中华文明,这就仿佛一条大河,“支流”最终汇集成“主流”。根据南北各地龙山时代人群的遗传差异性,分为“东方模式”和“中原模式”、“北方模式”、长江模式”,有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和技术交流可以在不伴随大规模人口迁移混合的情况下发生,有的不同地区和民族间的人口流动和基因交流、文化交流。
论文主要介绍陶寺王族、庐山峁贵族的古DNA,却对殉人DNA轻描淡写。
1、数年前,在石峁遗址祭祀灰坑提取到的一例人头DNA样本SM_K4_1,属父系N1-F963(最终确认为N1a2a1a1-CTS2959,正是姬周王族的上游型),推测殉人SM_2(N1a)应该和SM_K4_1是同族,都是N1a2支系,偏离齐家古人、庙子沟古人,可能有古匈奴成分,符合姬周祖先自传:不窋到古公亶父共十代均窜于戎狄之间,清晰说明姬周祖先老家不在中原,而是北方边远地区(姬周N1a2a-F1998迁徙与演进的考古学证据链)。女性贵族SM_1的常染成分接近河南仰韶古人,殉人SM_3(M117/F8)介于中原仰韶古人(河南仰韶中期)与庙子沟古人(内蒙古仰韶中期)之间。
2、庐山峁贵族墓主LSM_1(N1b2-M1819)偏离过大,含有较多的古东北亚成分,明显偏北。而他的殉人LSM_4(也是N1b2-M1819)常染成分介于中原仰韶古人与中原龙山古人之间,比较偏南。殉人LSM_2(M117/F8)接近齐家古人,女性殉人LSM_3介于中原仰韶古人与庙子沟古人之间。
3、 陶寺王族墓主TS(F114/F46)接近齐家古人。
复旦私定的版本Oα、Oβ,分别是O2a2b1a1-M117支系F8、O2a2b1a2-F114支系F46(具体指明:仰韶人F2887)。
庐山峁男性贵族墓主LSM_1(N1b2-M1819+G2a1g),他的旁边有三个殉人:男性LSM_4(N1b2-M1819+M10a1)、女性殉人LSM_3(M10a1)、男性LSM_2(M117/F8+D4)
埋在石峁城石墙中的两个牙齿,分别是SM_2(疑为N1a2-F1998支系)与SM_3(M117/F8),应该是用于祭祀的人牲,因为石峁人在石墙中放玉器、人性,是一种祭祀行为,祈求神灵的庇佑。
石峁城址建筑物基址下面和墙壁中间埋藏和塞置的玉器、人殉或者人性,以及石雕人头像、菱形眼睛、精美石雕,还有疑似祭坛的发现,说明在石峁古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雏形的宗教系统:石雕人头像是全体教徒信奉的万能神灵,石峁统治者是高居顶端的教主,而居于统治者之下的是一个掌握教权的巫觋阶层。
庐山峁、石峁、陶寺的常染成分,可模拟为中原仰韶人YR_MN、黑龙江古人AR_EN和裕民古人Yumin的混合。陶寺王族墓主TS(F114/F46)含有20%的东北亚ANA成分。庐山峁贵族墓主LSM_1含有近50%的东北亚ANA成分,竟然超过西辽河红山人WLR_MN。
因此,齐家古人、庐山峁古人、石峁古人、陶寺古人、中原仰韶村龙山人,都与庙子沟古人(内蒙古仰韶中期)、五庄果墚古人(陕北仰韶晚期)具有密切的遗传关系,他们的常染成分高度相似,都含有较多的古东北亚ANA成分,跟红山古人的关系特别近。
河北省郑家沟遗址红山古人共有14例男性标本,其中C2b1a1a2-ACT7091共12例,是华北地区常见C2b1a1a1a-M407的兄弟支,但与鲁北大汶口人C2b1a2a-F1319分化了一万年;还有N1-Y109387一例,不知是N1a北支还是N1b南支。N1a1a2-Y162952支系Y109387一例,这个单倍群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区,是西伯利亚人N1a1a1-M46的兄弟,这一支系曾出现于即墨北阡遗址。
郑家沟红山古人与西辽河红山人之间具有最密切的遗传关系,并且与鲁北五村/傅家大汶口人关系密切。
郑家沟红山古人的常染成分,可模拟为内蒙古新石器早期裕民古人与鲁北五村大汶口人的混合。
2025年06月河北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等团队合作发表的《Genetic formation of Neolithic Hongshan people and demic expansion of Hongshan culture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报告论文,通过对河北郑家沟遗址19例红山文化相关个体的全基因组分析,解析出红山人群的三重遗传成分:古东北亚成分、仰韶相关成分和山东后李相关成分。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红山个体中约53%可追溯至鲁北傅家、五村大汶口人群的贡献。这一发现修正了考古学假设——红山文化的形成并非仰韶农民直接北上,而是通过大汶口文化中介实现的基因流动。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中新石器时代辽西、中原与山东之间复杂的基因交流网络:黄河中游的农业人口并非直接北上,而是通过山东大汶口文化向东北方向迁移,与当地古代东北亚人群混合形成红山文化人群。
据此推测,郑家沟红山古人、西辽河红山古人向黄土高原迁移,使得晋陕北部仰韶人群遭受遗传冲击,带来了更多的遗传多样性,同时深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高地龙山人群。
五庄果墚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简介
相比于汪沟古人,五庄果墚仰韶古人的血统复杂得多,含有较多的古代藏人、黑龙江古人成分。
《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
陕北仰韶晚期-五庄果墚遗址的常染成分非常分散,有的接近蒙古人、有的接近匈奴人、有的接近藏人,与齐家古人、庙子沟古人(内蒙古仰韶中期)、河南仰韶村龙山人一样都含有较多的古东北亚ANA成分,凸显出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人群的血统复杂性。
仰韶村龙山人、齐家古人、庙子沟古人的古东北亚ANA成分较多。
基于成对qpWave模型否定了河南仰韶村龙山人群与汪沟仰韶人群在遗传上具有亲缘关系的模型。F4对称性测试表明,与汪沟古人相比,仰韶村龙山期人与古代藏族、古代东北亚人(即黑龙江古人ANA)相关的祖先有着额外的遗传亲和力。不过,qpAdm 建模表明,仰韶村龙山期人可以建模为 ANA(11%–17%)和汪沟(83%-89%)相关祖先的混合,几乎不含古代南方人血统。
仰韶村遗址龙山时代人群的分析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
1,豫西地区龙山期人群,依旧保持着当地仰韶期人群的遗传面貌,这是一种当地既有的、延续至少数千年历史的常染遗传格局,本身就比郑州附近的人群(汪沟)更北。
2,豫西地区龙山期人群,原本血缘格局同郑州的人群(汪沟)差不多,但遭受晋陕北部龙山时代人群(黄土高原山地居民)的遗传冲击,高地龙山人在大肆扩张,带来了更多的遗传多样性,改变了豫西既有的常染格局。
庙梁(Miaoliang)和五庄果墚人群(Wuzhuangguoliang)均属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距今4500~5000年
陕北石峁遗址等172例居民样本的古基因组分析显示,其与陕北仰韶文化晚期庙梁(Miaoliang)和五庄果墚人群(Wuzhuangguoliang)的遗传联系最为紧密,体现了其遗传的连续性。庙梁/五庄果墚、石峁人群的常染重合性,本来是同一族群的分支,介于蒙古、藏人与北汉之间。23魔方、微基因数据表明,现代陕西甘肃汉族大多数都是由北汉65%、南汉15%、藏缅10%、蒙古10%、混合的,并非秦汉以来混合形成的,而是与仰韶文化庙梁和五庄果人群、石峁人群大体一致,具有遗传的连续性。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汪沟遗址的古基因组学研究》
内蒙古乌兰察布5500年前的庙子沟仰韶古人,陕北靖边5000年前的五庄果墚仰韶古人,陕北4200年前的石峁龙山古人,他们的常染色体关系挺近的。特别是五庄果墚古人这一人群挺复杂的,有一部分和红山古人有联系,有一部分和庙子沟仰韶古人、喇家齐家古人有关系,还有一部分跟汪沟仰韶人有关联,另外一部分则和石峁人有关。不过,他们的常染成分与现代北方汉族的遗传距离明显大。考古学者认为喇家齐家文化主要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陇东南并与菜园文化融合的结果,那么4300年前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古人跟5000年前五庄果墚的古人,基因是挺相似的。
从已知的单倍群数据来看,庙子沟、五庄果墚、石峁这些地方有不少C2b1b-F845和N1b2-M1819,均是泛中原地区的土著。说得更具体点,他们大概是西辽河到甘青那一带高地上的土著,高原生存条件差,资源不丰富,导致他们的人口数量比不上黄淮海平原的O2-M122农业人群。
黄河中游河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因水土流失,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是草原和灌丛。由于降水量少,土地贫瘠,植被生长相对较差。大部分地区植被以短命草本植物为主,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农业经济落后。加之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黄土高原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全国的落后水平。数据表明:黄土高原覆盖面积达64万平方公里,纵横交错的沟壑多达27万条,曾被联合国认为:该地区无药可救,并不适合人类居住。考古表明,黄河中游山西地区的前仰韶时代文化的缺失,在与山西临近的陕北河豫西地区,少有前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很可能同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恶劣的地理环境有关。因此,“黄河中游农业人群”伪概念,纯属子虚乌有。《再次批驳文少卿团队所谓的“黄河中游农业人群”伪概念》
结论:
新石器早期裕民相关人群,新石器中期红山古人向黄土高原迁移,使得晋陕北部仰韶人群遭受遗传冲击,带来了更多的遗传多样性,形成了庙子沟、五庄果墚、庙梁等高地仰韶人群。新石器晚期,高地仰韶人群深受大汶口文化的冲击影响,形成了高地龙山人群,依旧保持着当地仰韶期人群的遗传面貌。因此,有些论文声称高地龙山人群的常染变化,是开始遭受裕民/黑龙江相关人群的遗传冲击而导致的,而不是来自当地仰韶人群,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发布于:北京市按月配资.股票杠杆交易平台哪个好.个股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